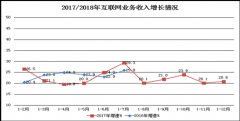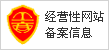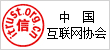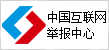|
国内最大“寄血验子”案背后的入刑之争|参与孕妇超5万,有人鉴定性别后引产
周敏告知她们胎儿性别鉴定结果时并不明说男女,而是说和老公性别一样或者与孕妇性别一样。其中,4名孕妇得知胎儿性别后选择引产,被引产的胎儿性别两名为女孩、两名为男孩。
▲2018年3月23日,郑州一家医院B超室外的墙上张贴的“禁止胎儿性别鉴定”的宣传标语。但对于非医学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是否入刑,目前还存在争议。图/视觉中国 警车开到家门口,李玲才知道自己是逃犯。 她曾是深圳“爱心爸爸”公司的网络推广员,在网上发布可以提供赴港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等医疗信息,为公司招揽客户。 这家公司因为给客户提供赴港胎儿性别鉴定中介服务,被警方查处。公开报道显示,浙江永嘉警方调查发现,预计参与寄血验子的孕妇超过5万人次,涉案金额达2亿元以上。永嘉县公安局陆续将60余名涉案人员挂上网逃系统,李玲就是其中之一。 这起轰动一时的“寄血验子”案,涉及浙江省部分孕妇,包括李玲在内的数十名业务人员被浙江警方以“非法行医罪”立案调查。 随后,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将部分涉案人员以“非法行医罪”判刑。 事实上,对于非医学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导致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行为,我国相关法律将其界定为行政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但2012年11月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部分罪名定罪标准的92条意见,将上述行为认定为非法行医,须追究刑事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左坚卫认为,浙江地方法院在判决中引用了浙江高院相关规定的条文作为定罪的规范性依据,判决是有问题的,因为刑事判决据以定罪的法律依据只能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刑法规范和司法解释。 他表示,如果地方法院认为需要对法条进行增补或有权解释,只能报请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立法或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其自己制定的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强行要求下级法院执行。 关于此案的上述行为,今年7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室回复法学家李步云意见的复函中明确提到,将督促有关部门纠正地方法院越权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表示将于近期通知辖区法院停止执行意见第九十二条有关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行为以非法行医罪处罚的决定。 非医学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是否入刑,一直以来存在争议。多名法律专家认为,立法要有前瞻性,要根据目前生育观念等社会问题的发展趋势,是否有必要将此行为入刑,是一个需要长远考虑的问题。
▲深圳“爱心爸爸公司“寄血验子”案”。新京报制图/高俊夫 寄血验子孕妇超过5万 李玲今年30岁。2011年,她进入深圳“爱心爸爸”公司。一开始的业务是租房销售,到了2014年,她被调到公司的优乐部门,工作内容是在网上发信息,为公司招揽有赴香港打疫苗、基因检测、胎儿性别鉴定等需求的客户。 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判决书中显示,2013年开始,该公司老板林伟强(另案处理)在公司内设立康健、唯康、卓健等业务部门,为全国有胎儿性别鉴定需求的客户提供中介服务。公司的优乐、港欣、优诚、正大等网络部门,在网上发布信息招揽全国各地合作商与客源,为业务部门提供客户信息。 新京报记者联系曾在上述公司工作的多名业务员得知,胎儿性别鉴定只是公司的其中一项中介业务,该公司还有香港教育、租房、代购、保险等中介业务。 张芳所在的部门叫“康健”,在收到“优乐”等网络部门给的孕妇电话后,她会打电话过去谈单,并将愿意赴港的孕妇名单登记下来,再让预约业务员做进一步安排。张芳透露,公司与香港两家诊所对接,对于不熟悉地址的孕妇,还有人带路过去。 对于不方便亲自去香港的孕妇,张芳表示,她们会建议孕妇找当地医生抽血,寄到深圳,再由公司其他部门送到香港化验所。 孕妇通过上述公司在香港做胎儿性别鉴定,需向公司交纳三千、四千不等的中介服务费。但如果是由浙江永嘉一位合作人介绍,价格为一千元。 “每个部门其实是一个小公司,我们网络推广只有四五个人,跟其他部门的不联系。”李玲表示,她们当时也有疑惑,担心发布这样的信息违法,“问了以后,公司法务跟我们说胎儿性别鉴定在香港是合法的,我们就这样干下去。” 每成功一单胎儿性别鉴定服务,具体业务人员可以拿到100元提成。李玲工资低的时候三四千,高的时候有八九千。“香港那边鉴定后,直接电话告诉孕妇,后面的事我们就不清楚了。”李玲说。 2015年3月,浙江永嘉的合作人被查,上述公司被浙江警方发现,并立案调查。公开报道显示,浙江永嘉警方调查发现,初步预计参与寄血验子的孕妇超过5万人次,涉案金额达2亿元以上。包括在深圳抓获的11名人员在内,目前已有75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采取了强制措施,主犯林某等其他嫌疑人已经被批准上网追逃。 有孕妇鉴定性别后引产 在浙江永嘉与深圳“爱心爸爸”公司合作的人叫李中(化名)。 浙江台州玉环人李中,曾是玉环县人民医院的职工,因故被开除后,在当地开了一家药店。2014年,李中通过网上搜索了解到深圳“爱心爸爸”公司提供香港寄血验子服务。李中因自身的医学背景成为“爱心爸爸”在当地的代理人,他介绍的孕妇遍及台州、乐清、永嘉等地。公开报道显示,截至落网,李中非法获利数十万元以上。 公开报道显示,2015年初,永嘉警方联合当地计生部门在开展“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排查执法中,发现李中与深圳公司的上述行为,遂介入调查。 李玲告诉新京报记者,2015年12月25日,公司突然通知放假,她回了老家,听说部门的同事被抓,但不清楚具体情况。 与此同时,警方还发现另一名合作医生周敏(化名)。周敏同样是通过网络联系,成为深圳“爱心爸爸”公司合作人。周敏是乐清某民营医院职工,起初周敏在医院办公室内替上门的孕妇提供抽血服务。后来,她更换手机号码,专门在外租房为孕妇抽血以躲避打击。永嘉县人民法院判决书显示,周敏没有医师执业资格。 永嘉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8月份至2015年6月份期间,周敏在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情况下,在乐清市一家民营医院或附近居民房内为16名孕妇抽取血液,并将血液寄往广东省深圳市为孕妇进行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每次收取鉴定费用5500元至6500元不等,非法获利30000元以上。 16名孕妇在作证时表示,她们与周敏通过电话联络,周敏表示自己所在的医院和香港长期合作,可以随时通过验血来鉴定胎儿性别。周敏告知她们胎儿性别鉴定结果时并不明说男女,而是说和老公性别一样或者与孕妇性别一样。其中,4名孕妇得知胎儿性别后选择引产,被引产的胎儿性别两名为女孩、两名为男孩。 2017年3月30日,永嘉县人民法院判决,周敏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公司一名业务员告诉记者,除浙江外,公司在其他省份并没有合作人。但浙江永嘉县人民法院判决书显示,这家公司多个部门先后为广东、福建、浙江、海南、四川、湖北、湖南、广西、山东、辽宁、山西、河南、北京、上海等省份的孕妇提供过赴港胎儿性别鉴定中介服务。
▲警方调查发现,参与验子孕妇超过5万人次,涉案金额达2亿元以上。网源图片 深圳业务员被分批处理 警车开到家门口时,李玲才知道自己是逃犯。2016年1月,李玲在山东老家被抓。 “我在永嘉看守所呆了半年后取保候审,警方觉得我2011年就进公司了,肯定清楚业务,但我是2014年才接触,业绩也不好,当时主要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李玲说。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2015年12月22日起,永嘉县公安局陆续将60余名涉案人员挂上网逃系统,李玲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只有个别几人还未到案。由于人数众多,永嘉县警方将案件分批处理。 深圳“爱心爸爸”公司其中一位业务员的辩护律师——广东礼磊律师事务所曹铮介绍,2016年3月18日,永嘉县公安局将第一批抓捕的14人向永嘉县检察院提请起诉。2017年12月,永嘉县法院宣判第一批10人犯非法行医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到一年半不等,4名缓刑。部分人提起上诉。 判决书显示,永嘉县人民法院判决时法律适用解释认为《刑法》规定的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情节严重”的四种具体情形外,还规定了“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将“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认定为非法行医罪“情节严重”的标准,符合法律规定。 记者注意到,这里提到浙江高院认为属于非法行医罪“情节严重”的标准,源自浙江省高院2012年11月9日出台的《关于部分罪名定罪量刑情节及数额标准的意见》,其中第92条的第5、6项规定表明,“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3人次以上,并导致引产的”;“因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该行为的”,均属于“情节严重”,构成非法行医罪。 曹铮律师认为,这一点适用法律错误。《刑法》336条第一款及其司法解释并没有“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的规定。《意见》第92条对《刑法》336条第一款构成非法行医罪“情节严重”的五条司法解释擅自增加了两条“解释”。 “按照立法法,浙江高院无权制定司法解释,因而《意见》第92条是非法的、无效的。”曹铮律师说。 事实上,早在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中就曾讨论将“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导致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行为入刑。 公开报道显示,当时草案修正的专家意见产生了分歧。反对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有复杂的社会原因。重男轻女的观念问题是不能也不宜用刑法手段改变。赞成者则认为,用刑法手段对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加以打击,能够起到震慑遏制作用。最终这一草案没有通过。 2016年3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会议讨论通过《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这一规定将“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确定为行政违法行为。 在庭审中,曹铮律师将这些情况一一解释,“法庭上没人反驳,但也没人理睬我们的话。我会见时,业务员说知道了我们没罪,到了法庭上却都认罪了。”曹铮说。 纠正地方法院越权司法解释 曹铮律师团队在网上查询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在浙江省34个市县级法院已判处实施“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的215个人犯有非法行医罪,涉及143起案件。 在这143起案件中,有5个判决书的法律依据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部分罪名定罪量刑情节及数额标准的意见》及《刑法》336条第一款。 判决书所认定的犯罪事实均是案犯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无堕胎后果的也当此罪。其中通过寄血到香港化验的方式鉴定胎儿性别的判决共有19例,通过B超鉴定胎儿性别的判决有12例,通过抽取静脉血化验鉴定胎儿性别的判决3例。案犯均处有期徒刑三个月到二年八个月之间,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到十万三千元之间。 而在行政处罚中,根据《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对介绍、组织孕妇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曹铮律师请中国刑事法律研究院高明暄、赵秉志等5位专家写了一份法律意见书,他们一致认为“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是行政违法行为,不是非法行医的犯罪行为,不构成非法行医罪。 专家们认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地方司法机关无权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公安机关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行为作为犯罪处理所依据的地方司法机关解释性文件,不能作为量刑的依据。 曹铮告诉记者,他们为此曾向浙江公检法、两高、公安部、浙江省和全国人大寄出55封信反映浙江地方法院在诉讼中适用法律的错误。但遗憾的是,只有一次回应。今年3月份,浙江高院收到全国人大转办的信后给他打电话表示,“我们高院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我问打电话的女同志符合哪个法律规定,她就不说话了。”曹铮说。 曹铮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希望他帮忙提出意见。李步云于今年1月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指出地方法院越权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问题。 2018年7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室给李步云回复称已对提出问题进行研究,与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作了沟通、并征求了有关方面意见。复函中表示,据反馈情况,浙江省高院表示《意见》属于应当清理的带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将商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停止执行相关条款,共同研究妥善处理正在审理的案件及生效案件,并将于近期通知辖区法院停止执行《意见》第九十二条有关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行为以非法行医罪处罚的决定。 事实上,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复函李步云之前,2018年6月7日,浙江省高院已发布通知,要求省内各级法院停止执行意见第九十二条有关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行为以非法行医罪处罚的决定。 是否判刑依然待定 《刑法》336条司法解释规定,非法行医罪“情节严重”的情形,最后一条为“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张芳们担心,自己将依据这条兜底条款被判刑。曹铮律师认为,浙江高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是利用了兜底条款中的其他情形进行自由发挥,违背了国家法治统一的基本思想。 2018年3月8日,永嘉县检察院对第二批25名人员提起公诉。 王云属于第二批,听说自己被网络通缉,她于2016年底自首。“爱心爸爸”网络推广是王云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最开始发教育留学的广告信息,后来发胎儿性别鉴定的。” 2018年4月25日,永嘉县法院公开审理王云等人。王云说,法院指定给我们的援助律师说只是行政违法,不是非法行医,法官当时也没有理睬。案件没有当庭宣判。 王云在庭审中认罪。“不认罪又能怎样?判刑的话还能尽快结束。现在随时可能会被法院叫过去,根本不能正常工作,”王云说,“这件事已经拖了快三年,我感觉人生都荒废了。” 2018年7月16日,包括王云在内的第二批17人(11人取保在外,6人收监)收到法院通知,称下周开庭宣判结果,让她们去交罚金(16人分别各缴纳4万,1人3万)。但目前仍未等到宣判。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左坚卫解释,刑事司法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每个罪名都有自己独立的构成要件。非医学需要的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行为要构成非法行医罪,首先要符合该罪的主体要件。 他表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即行为人必须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这就涉及如何理解“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问题,有人认为有医师资格证但没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甚至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超范围执业都属于“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 此外,非法行医罪中的行医行为一般指的是诊断治疗疾病的行为,至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是否属于非法行医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左坚卫认为,浙江地方法院在判决中引用了浙江高院相关规定的条文作为定罪的规范性依据,判决是有问题的,因为刑事判决据以定罪的法律依据只能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刑法规范和司法解释。如果地方法院认为需要对法条进行增补或有权解释,只能报请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立法或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其自己制定的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强行要求下级法院执行。 他表示,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是否入刑,需要考察该行为当前的危害性及未来发展趋势。如果目前已经很少有孕妇及其家庭成员因为重男轻女而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并随后对女性胎儿选择堕胎,那么,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就不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就无需“入刑”。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对于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加大处罚是有必要的,但是否入刑还需要相关立法部门进一步研究。 “非医学胎儿性别鉴定曾有专家呼吁纳入刑法,地方对于个案可能有刑罚处理。目前入刑的法律依据并不十分充分,这块还没有大的进展,查处难度、掌握证据难度比较大。”陆教授说,“全面开放二胎后,性别比有所下降,立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能在短期内改变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要想调节性别比,需要塑造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包括女孩的生存、教育、就业权利给予充分重视,这样的话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
热门关键词: